在古老星图下辨认自己
——读傅佩荣《国学的天空》
字数:1294
2025-09-03
版名:悦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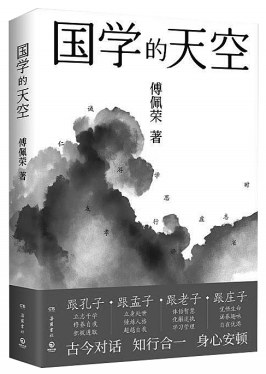
□魏咏柏
在台灯柔和的灯光下,翻到这本书第300页的留白处,我忽然想起15岁那年,一个泛着旧书霉味的黄昏。我蹲在巷子尽头的旧书摊前,手指无意间触到一本泛黄的《庄子》。翻到“浑沌之死”那一页,四个字像生了锈的铁钩,猛地扎进我心里。那时候的我,还读不懂这则寓言真正的重量。
很多年以后,傅佩荣先生用他素净的文字和从容的笔批注,才为我解开了这个迷局。他说:“七日凿七窍,被凿穿的哪里是浑沌本身,不过是我们非要强加给它的、那些自以为是的意义罢了。”那一刻,仿佛有个结突然松开。
读《国学的天空》,有点像看一位老师傅不紧不慢地修复一件老器物。傅佩荣从不拿“博大精深”这样的大词来压人,反而在一些细微处,轻轻一点,就让你恍然有所悟。比如,他讲《论语》中“天何言哉”,不搬弄玄奥理论,却说:“你去看清晨菜叶上滚动的露水,天道就在四时运行、万物生长之中。”谈到孟子“见牛未见羊”的那一丝心软,他写道:“那一瞬间的不忍,比多少仁政学说都更接近善的本质。”
我尤其喜欢他把国学比作“天空”。是啊,这片繁星满布的夜空,从不要求人跪拜——它只是安静地在那里,等待每一个仰望的人,与某颗星星悄然对视、会心一笑。
让我反复回味的,是书中那些打破东西方哲学壁垒的段落。傅佩荣早年钻研西方哲学,尤其在耶鲁苦读的经历,反而让他更清晰地看见老庄思想中锋利的刃光。他认为,《齐物论》里“大块噫气”的苍茫,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之问”遥相呼应;而孟子所谓“浩然之气”,不是什么虚空的口号,是生命真正充沛时能够体验到的一种实在状态。
他对“庖丁解牛”的重新解读,我也特别喜欢。他认为,这不是什么神秘绝技,不过是一个劳动者在重复了千万次的动作中,突然捕捉到了某种贯通本质的直觉——“批大郤,导大窾”,刀锋游走之处,早已超越了骨肉间隙,直抵现象背后的真理窄门。
有些片段读起来特别亲切,就像跟一个懂你的老朋友深夜聊天。比如,谈到孔子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傅先生说,何必批评圣人,他不过是坦然说出了大实话。而谈到庄周梦蝶,他悠悠一问:谁又不是困在梦中的蝴蝶?偏偏要较真醒来,计较是庄周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变成了庄周。
当然,阅读中也有不少让我卡住、又忽然畅通的时刻。最初读老子“天地不仁”时,正逢南方梅雨。阳台那株茉莉被急雨打得七零八落,花苞沾在青石地板上,像破碎的月光。我正为这凋零感到可惜,突然明白了傅先生所说的“慈非仁爱”——天地并非无情,只是它的慈悲远超我们狭隘的善恶标准。凋落的花苞与新发的嫩芽,在“道”的注视下,本是生生不息中同等珍贵的存在。合上书时,雨恰好停了。低头看见水洼里摇曳的月亮倒影,仿佛也多了几分温柔。
现在,这本《国学的天空》就斜插在我书架最显眼的地方,书脊已经被我翻得有些松垮。有一天,一位朋友来家里,看到这本书,半开玩笑地问:“这算不算另一种成功学?”我愣了一下,随即想起傅先生写孔子困于陈蔡却依旧弦歌不绝的那段——不是在困境中硬撑乐观,而是君子可以身处贫困却不被其困住。精神的出口,从来都由自己定义。
我从书中抽出一页笔记纸递给他,上面抄着我最喜欢的一句:“我们这一生,不过是在古老的星空下,慢慢辨认属于自己的星轨,学着如何随风而行,自在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