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茧之痛与心灵之光
□何 玉
字数:1515
2025-08-13
版名:师阅知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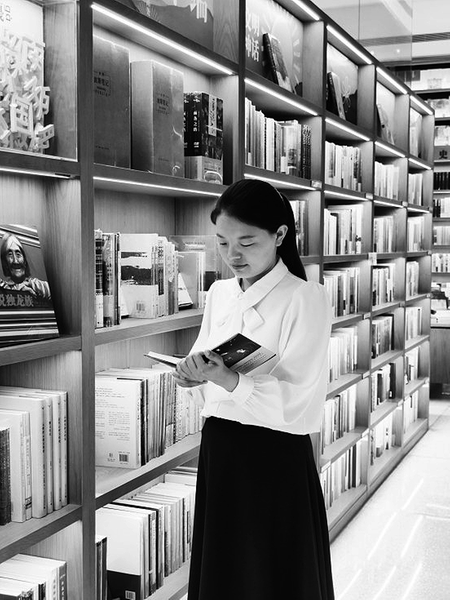
那堂七年级的 This ism ysister公开课,是我教学生涯的一道疤。四年前,作为学校初中部临聘教师兼教研组长,我抱着教案在空教室里演练到深夜,FamilyTree的彩色卡纸在黑板上拼出理想中的课堂图景:学生们围坐讨论、畅所欲言,评审专家的笔记本上落满肯定的批注。然而现实是,当铃声响起,45双眼睛与我对视的瞬间,所有预设的环节都凝固成沉默的窒息。
恐惧之墙:
当教学沦为技术展演
磨课时,教研员那句“流程太僵化,学生参与度为零”,让我在办公室里哭到发抖。直到翻开帕克·帕尔默的《教学勇气》,我才惊觉那场失败早有预兆——书中描述的“教师内在自我的分裂”,正是我当时的镜像:用PPT动画掩盖紧张,用频繁的提问试图激活课堂,却始终没敢抬头看学生眼里的茫然。我把全部精力都耗在“完成评审指标”上。
“恐惧在师生间筑起高墙”——我的恐惧是怕评审否定自己的职业价值,学生的恐惧则是怕回答错误被嘲笑。两种恐惧织成密不透风的茧,让本该流动的语言课堂成了死寂的真空。
破壁之钥:
从技术回归心灵的教学实验
考编成功后,我成为一名高中英语教师。我把《教学勇气》夹在备课本里,在扉页上写下“看见学生,先看见自己”。第一次尝试“心灵预习”是在教MyDream阅读课时,我没有急着划分段落结构,而是先在课堂上分享自己的成长故事。后排那个总打瞌睡的男生突然抬起了头,下课时塞给我一张纸条:“我想当汽修工,但我妈说没出息。”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讲定语从句那节课上。当学生提出课本未涉及的“theway+从句”用法时,我不再像从前那样强行绕开,而是在黑板上画了个问号,“这个问题老师也需要查证,课后我们组织个‘语法侦探小队’如何?”第二天,竟有7个学生带着不同的语法书来到办公室。“伟大事物”在此刻显形——不是预设的教案,而是师生共同探索知识奥秘的热情。
我开始在课后发“心灵反馈条”。有个学生写道:“您上次说自己学定语从句时也卡壳,我突然就不怕犯错了。”这句反馈让我想起四年前那节公开课上那个在FamilyTree旁画小狗的男生。在我的不断努力下,这个小男孩也发生了改变。后来,他在“家庭故事写作”中写道:“我家的Family Tree少了爸爸,但老师说每棵树都有独特的生长方式。”当教师敢于暴露脆弱,课堂才能成为学生心灵安全的栖息地。
读写转化:
在文字中完成教学救赎
写作成了自我疗愈的过程。当我把公开课上那个孩子低头画FamilyTree的细节写成片段时,突然意识到:那时若能蹲下身问一句“你画的爷爷奶奶有什么故事”,或许就能敲开沉默的裂缝。
这种反思催生了“三维备课法”:知识维度梳理教学目标,心灵维度预设学生情感节点,自我维度记录个人经验联结。在教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时,我不再逐句分析隐喻,而是播放了一段自己朗读的录音,讲起大学时为翻译这首诗熬夜的傻事。当学生们笑着争论“夏天的日子”到底是热烈还是短暂时,那个经常在课堂上保持沉默的女生突然举手说:“我觉得诗人是用夏天的易逝反衬爱的永恒。”她眼里的光,与四年前课堂上的死寂形成对比。
心灵在场:
教育最本真的模样
这个暑假整理旧物时,我翻到公开课那天的教案,纸页间夹着一片干枯的枫叶——那是后来学生送的毕业礼物,背面写着:“老师,现在我们不怕说英语了,因为你让课堂像家一样。”帕尔默说:“教学的生命力在于教师的自我认同。”如今我才真正懂得,当教师不再扮演“完美教书匠”的角色,敢于把真实的自我带入课堂时,知识才能从冰冷的符号化作心灵的养分。
上周听一位年轻教师的公开课,看到她在学生卡壳时自然地说“这个话题老师也纠结过,咱们一起聊聊”,突然想起四年前那个秋日的教室。教育的真谛从来不在行云流水的示范课里,而在师生共同穿越困惑的勇气中。那堂失败的公开课,最终让我明白:最好的课堂,是教师用完整的心灵点亮学生心灵的过程,而《教学勇气》这本书,正是指引我们在黑暗中看见彼此的那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