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水为文不受尘
——读张彦梅散文集《生命的回声》
字数:1386
2025-07-09
版名:悦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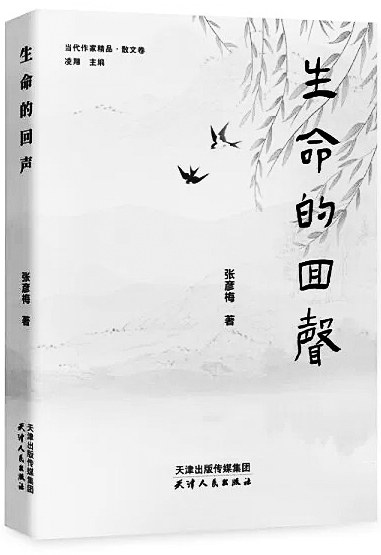
□梁新会
在我眼里,爱好写作的人大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一类是心口不一,言不由衷。
张彦梅完全属于第一类。
《生命的回声》开篇是《春野》。阳春三月,张彦梅像个孩子似的,满心欢喜地在田野里漫步。荠菜花、婆婆纳、蒲公英、车前草,令她目不暇接。她想起《诗经》里的“薇”。“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千百年前的伯夷、叔齐、苏东坡、陆放翁都曾是采薇人。而如今,采薇者鲜见矣!这些植物在《诗经》里的模样或清晰或朦胧,但都用质朴无华的身影,让诗词曲赋薪火相传。“一种静气在体内安营扎寨,胸口似乎有火苗蜿蜒。”她提着一篮春鲜,手捧荠菜花,喜滋滋地回到家中,“洗手作羹汤”。这篇美文便自然成形了。
这就是张彦梅的生活和写作状态——本真自然,思绪万千,表达却有节制。
在《菖蒲之风》里,她发现菖蒲的美好从诗句中流入了朋友的书房。菖蒲无论是孤植,或是与石、苔藓组景,皆俊秀卓然,不愧为花草四雅之一。她在《冬日花开不唯梅》里,写了枇杷冬天开花带给她的惊喜。我家门前曾种有一棵枇杷树。多年前,弟弟从南方寄回了一箱白玉枇杷,果肉橙红透亮,父亲赞不绝口,居然用果核种出了枇杷树。每到冬天,父亲都要用大大的塑料袋将枇杷的枝叶包裹起来,枇杷树就像一个特大号棒棒糖矗立在院中。但我从不知道枇杷“秋日养蕾,冬天开花,春来结子,夏初成熟”,是“果木中独备四时之气者”。而张彦梅却从枇杷全身皆可入药中,悟出了这是“寒暑皆历,默默耕耘,一点点累积的结果,也是光阴的馈赠”。
张彦梅热爱生活,她书中写自然万物的篇章很多。比如《托起明天的晨曦》《苦楝树》《五月榴花照眼明》……我国古代文人对“清、淡、拙”的东西一直情有独钟,张彦梅也有这样一种清雅淡定之气。她的文章质朴天然,先从好奇起,再将心中所思所想娓娓道来,结尾巧妙自然,画龙点睛,令人回味无穷。她在《冬意隽永》里写道:“我是自然界的孩子,我的良心永远是纯洁的。我想修炼成植物的性格。这是冬赐予我生命的底色,并在生命里隽永。”
张彦梅在充满书香气息的家庭长大,耳濡目染喜欢上了读书和写作。她骨子里亲山乐水,在“荒地”里散步时,送菜老人的一席话引起了她的思考——心灵也是一块闲置的荒地,你不种庄稼,它就长杂草。她向往一切美好的事物。在逛街时,她写下了《楼上楼下》,开头那句“品牌落寞和美人迟暮一样令人叹息”,艳惊四座。她欣赏质朴天然,鄙夷虚荣浮夸。在《吾质本朴》里,她拒绝纹眉、垫鼻子,明确表示这与她从小崇尚的“质朴为美”观念相去甚远。
苏童谈散文时强调:“以情感人永远不过时。”张彦梅的作品真切天然,像清泉流泻,像秋风乍起,像花开花谢,不事雕琢,却自带光环。她是传统的,也是时尚的;是柔弱的,也是坚强的。这些不同的特质在她的文字里相映成趣。她在《四叔》里,讲述了四叔与四婶的传奇爱情,让我们看到了四叔这个从红色根据地走出的后生演绎的新一代陕北人的美好生活。在《悲情田小娥》里,她认为“田小娥属于传统女性(逆来顺受)与新型女性(独立自主)之间的过渡”,相较于兆鹏媳妇的压抑而死,抗争而死的田小娥具有更多的叛逆色彩和悲剧意味,“现代女性有完整独立的人格……不是某个男人的附属品。这样才能避免田小娥式的悲剧发生”。
这样的话语温暖真诚,是张彦梅的肺腑之言。一如她写的:“我不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我喜欢一切质朴的东西……希望我的小文传递的微光,温暖你、鼓励你!”